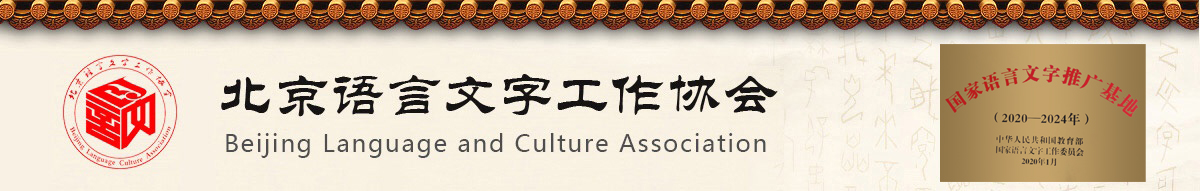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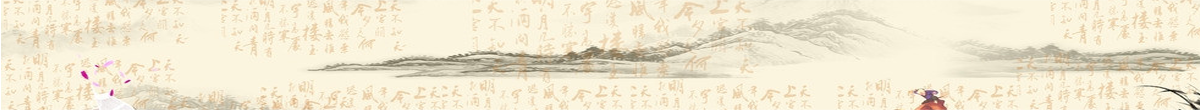

漢語語言知識當前位置:首頁 > 語言博覽 > 漢語語言知識 >
“六書”排序與漢字演進脈絡新探
來源:北京語言文字工作協(xié)會 | 發(fā)布時間:2017-07-30 23:21:02 | 瀏覽次數(shù):
東漢許慎撰著的《說文解字》是中國文字學的開山之作,對于文字學的發(fā)展貢獻居功至偉,備受后代學者推崇。但是《說文》作為一部漢代撰著的典籍,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受文獻資料和編排體例的局限也難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比如,過于體式化的據(jù)形聯(lián)系文字,將屬于同源詞關系的文字都按形聲格局歸部分開,掩蓋了詞與詞之間的同源關系。對形聲字的分析,多數(shù)為“從某,某聲”,割斷了詞的音義關聯(lián),使人不知詞的本義由來。由此可見,盡管研究《說文》和漢字的文章典籍汗牛充棟,但有些問題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為此,本文將就“說文”研究中“六書”的排序及漢字演進脈絡的過渡環(huán)節(jié)問題,從新的角度再做一些探析。
許慎在《說文》中系統(tǒng)地闡述了漢字的造字規(guī)律——提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六書”造字法,并在《說文解字•序》里對“六書”做了全面的、權威性的解釋。”這是很多著作介紹《說文》時對“六書”的一般表述。顯然,“六書”造字法為后世提供了透析漢字音形義關系的基本范式和門徑。但當這種范式被絕對化看待并廣泛效行時,出現(xiàn)闕誤也就難以避免了。
“六書”及其定義只是許慎對前代漢字造字法的概括性分類和解釋。其實在《說文》中,許慎在“六書”之外還列舉了其他一些造字方式,比如反文(匕、仉)、倒文(夊、屰),減筆字(夕、甪)、改筆字(刁、毋)??梢娫S慎并未把“六書”當作不二法門,至于后人拘泥于許慎對“六書”的解釋和排序倒是值得我們反省。對于那些非六書造字法我們不但不應忽略,反當特別重視。此外還有兩種漢字演進中的現(xiàn)象也值得注意,一是象形字加聲符(齒、鷄);二是象形會意字加形符(杼、笧、沒、燃、)。如果把這些現(xiàn)象和六書范疇的細分化結合起來考察,就不難發(fā)現(xiàn),漢字造字法演進有著一條由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到形聲,其間夾雜著反倒文、拆減文、改造文等過渡環(huán)節(jié),孳乳漸進的脈絡。
提出這樣一個漢字演進脈絡,主要是基于語言結構演進與認知結構演進對應一致的規(guī)律。無論何種文字,從認知思維的角度分析,都是抽象表現(xiàn)經(jīng)驗思維的具形媒介形式。漢字作為漢語的表征符號,其演進發(fā)展自然要受人認知思維由簡單到復雜、由具體到抽象規(guī)律的制約。漢字的形體演變,遵循的正是由簡單意象圖式到復合意象圖式的思維建構規(guī)律。也就是說,漢字及反映其造意具形模式的“六書”不會是跳躍出現(xiàn)的,它必然是一個由主體造意模式和過渡造意模式交叉間連構成、符合一般認知思維規(guī)律的演化過程。按照這一思路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六書”的漸進演化順序。
一、象形
《說文》的解釋為“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意思是說,按照物體的樣子將其形廓或特征用線條描摹出來。譬如日、月。象形字的擬制一般要經(jīng)過造意取象、具形征義的過程。按取象方式可分為輪廓象形(人、手)、特征象形(牛、羊)和關聯(lián)象形(石、眉)三種。象形字直觀形象,大多表征名物,排在造字法始位符合認知規(guī)律,也為大多數(shù)學者所認同。值得一提的是“反文、倒文”,如“匕”(跪人),仉(爪倒置表掌),從其直觀形象性看,應視為象形字,但造意具形已經(jīng)相對不再單純。特別是“倒文”雖然還是獨體字,但其造意已明顯具有很強的會意性。比如“屰”,其形象雖是一個倒置人形,但卻是“悖逆不順”這樣一個表示性向的抽象意義,可以說這已經(jīng)將具形征義手段用到了極致,于中不難窺見古人造意具形心智的提升和有意設計。
據(jù)此,我們可以把反文、倒文這一類改造字看作造字法突破單純象形局限,向指事、會意字過渡的聯(lián)系環(huán)節(jié)。象形是漢字的肇始之基,化育之本,其造意具形思維模式(以下簡稱造意模式)屬于主體性的簡單意象圖式。
二、指事
《說文》的解釋為“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意思是說,用提示性符號來指明所要表明的事物,讓人一看就能認出來,仔細看就能知道其意思,譬如上、下。以往都把提示性符號指明事物理解為兩種:一是在象形字上加提示性符號,如本、末、刃、寸、尤、;二是純用提示性符號組合的辦法造新字,如上、下、十。顯然,這是用加法思維理解指事的意思。許慎的定義只是說“視而可識,察而見義”,并無加減、改造筆畫之分,而且稱之為“指事”而不是“指示”。由此可見,像減筆字“夕(夜晚)”、改筆字“刁(叼)”、“毋(勿)”也都具有指事字的特征。
對于指事字應該提出兩點思考:第一,指事字有明顯的會意性質(zhì),其具形造意有了明確的細虛化表意和組合化構形訴求,指事字不多,但應該是表意造字方法推進的一個重要過渡環(huán)節(jié)。第二,純符號的出現(xiàn),標志著思維抽象化程度的提高,但造意具形功能不強,造字很少,也說明表意造字方法的發(fā)展已經(jīng)推進到了關鍵性節(jié)點。如果不產(chǎn)生突破,要么像古埃及象形字那樣,由于數(shù)量太少,擔不起為語言具形表意的重任而半途夭折,要么像閃米特人那樣從象形字中擷取表音符號轉向拼音文字的道路。指事的造意模式雖有進展,但仍屬簡單意象圖式,然而它也是引導象形向會意演進的重要過渡模式。
三、會意
《說文》的解釋為“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揮,武、信是也。”意思是說,用兩個或兩個以上能關聯(lián)的象形字或指事字作偏旁組成一個新字,將偏旁原來表示的意思以某種合理的拼合來表示一個新的意思。譬如武、信。如果聯(lián)系象形、指事中的改造性過渡字,會意字應該細分為三種:一是單體會意,如“正(到達目的地)”,反“正”為“乏(無力到達)”,“大(正面人)”變筆為“尣(瘸腿)”;二是同體會意,如從、森;三是異體會意,如秉、好、拾。
會意的出現(xiàn)對漢字發(fā)展具有質(zhì)變意義,會意的機理就是組合結構造成的構件“形素化”和整體詞義的“構效化”。所謂形素(字素),指的是本身具有音形義的字,在組合字中,由于結構的約束、激發(fā)和構件之間的相互作用,轉變成了隨機恰和詞義生發(fā)會意需要的義素構件。這種結構對構件原有性質(zhì)改變的現(xiàn)象稱為結構的素化效應。形素是從意會詞義角度的稱謂,它與形符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形符只是針對形聲字中的義符而言,不涉及會意字中構件生義問題;而形素則既針對會意字的生義構件,也針對形聲字中的形旁和有會意性質(zhì)的聲旁。所謂構效,就是結構方式的整體效應,是指會意字的詞義不是由其構件字義的簡單相加生成,而是由構件聚合產(chǎn)生的結構場化效應生成。
會意不僅僅是增加了一種具形征義的造字方式,而且創(chuàng)建了一種以偏旁為基本構件具有三重結構性生發(fā)新字功能的范式。具體說,一是形成了結構性意會詞義的構式效應。比如“林”的意思不是兩棵樹,而是一片樹;“利”不等于禾加刀,代表的是收獲。二是對既有文字利用上形成了結構性素化效應,造就了復合意象征義場,增強了動態(tài)抽象表義功能,比如“代”的造意角度是替換,是從木橛替人牽制牲口充當替手的動變角度征義;“戾”(彎曲)則是從看門狗見到生人俯身而吠的情態(tài)角度取義。三是調(diào)動激活了所用構件字的詞義和義素在組合字中的自恰性顯隱變換,拓展了其衍生新字的功能。比如在“數(shù)”(本義:清點)字中,“婁”的本義是頂簍,含有“積漸疊放”的隱性義素,比附用到表示清點入簍的動態(tài)特征上,這個隱性義素就被激活了。同時,構件字“攵”頻頻倒手入簍的隱形義素也被激活了。這樣,婁字原有的顯性義素、隱性義素與“攵”字的隱性義素高度恰和,構成一幅生動畫面。
總之,會意造成的結構性構式效應和素化效應改變了象形和指事字的功能意義,使它們在保留自身詞義充當行文語素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構造新字的形素功能,這樣通過排列組合便可極大擴充漢字的數(shù)量發(fā)展空間。會意的造意模式已經(jīng)上升為復雜意象圖式,在“六書”中應屬于主體造意模式。
四、假借
《說文》的解釋為“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意思是說,語言中有了某個詞,但沒有相應的字來記錄它,于是就從現(xiàn)有的字里面找一個音同或音近的字來表示它。典型的假借字有“其”(簸箕),借為代詞;“求”(皮毛大衣),借為欲求;“而”(絡腮胡子),借為連詞。一般認為假借算不上一種獨立的造字法,只是用字法,因為它并不產(chǎn)生新字,故而將其排在末位。但若從語言思維體系建構的過程性發(fā)展規(guī)律看,這種認識則有偏頗。應該看到,在漢字發(fā)展鏈條中,假借字是必不可少的過渡性發(fā)展環(huán)節(jié)和造意思維模式轉化的先導。假借是用字法,但它是對漢字發(fā)展路徑具有質(zhì)性轉變意義的用字法。從象形、指事到會意,漢字的發(fā)展一直在沿著依形表義的路徑在推進,這很容易把形義造字的模式固化,形成思維慣性,從而阻礙漢字的進一步發(fā)展。而假借出現(xiàn)的意義,就在于它打破了依形表義的定式約束,開啟了依聲表義的新途徑。具體說有三點很重要。
首先,本字被借用后在使用中容易與借字之間產(chǎn)生語義沖突,特別是用多了會造成理解障礙,這就促使人們必須想辦法解決這一問題,從而催生新的造字法并產(chǎn)生新字。事實也是如此,譬如當“求”字被借用之后,為避免歧義,便又造了“裘”字;“其”字被借用后,便又造了“箕”字,等等。
其次,假借的出現(xiàn)突破了依形表義造字法不利于表現(xiàn)虛詞和抽象詞的弱點,為完善漢語語法構式體系開辟了廣闊空間。從世界其他語言體系的發(fā)展情況看,借實為虛和實詞虛化也是完善語法構式體系的主要手段。
再次,如果說會意的出現(xiàn)造就了很多漢字孳乳新字的形素性功能,那么假借的使用則促發(fā)了更多漢字的聲符性功能。這對形成依聲索義的新習慣具有深遠影響,為形聲造字拓展了思路,鋪墊了基礎。假借是漢字演進過程中重要的過渡環(huán)節(jié),其造意模式與象形的造意模式一樣,也屬簡單意象圖式,只是其具形表義的媒介形式是語音而已。
五、轉注
《說文》的解釋為“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互受,考、老是也。”對于轉注的理解歷來眾說不一,本文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所謂轉注,就是把一個包含多種同類意義的字立為基本構件(建類一首),并將其中相同類義的某個具體意義轉授給另一個構件(字),組成一個組合字;同樣,另一個構件(字)在接受類首“轉授”的同類具體意義的同時也等于把自身某個同類的相應意義“注授”給了組合字(同意互受),二者共同構成一個新字。譬如考、老。
根據(jù)對許慎闡述轉注特征的分析,可以理解為,轉注就是通過給某個擁有多個義項的字加注其他類義符號而達成分形別義轉化生成新字的方法。具體可以從許慎給出的“老”字加以分析。“老”的本義為年老體衰,在甲骨文構形中突出的是垂發(fā)駝背的老人形象。但在實際使用中引申轉化成為:年齡較大、年壽高延、年老生殘以及經(jīng)驗多、德望重等包含了一系列義項的聚義字。為了在實際中區(qū)分類首字中的這些義項(類首,借“建類一首”化意),于是就以“老”為基本構件分別加注“丂”(拐杖)、“F(镸)”和“矢”(箭,甲骨文①形,②形改為“至”)分別組成:①考,在甲骨文中突出的是疏發(fā)持丂的老人形象,從“老”中分化出年壽高延為本義,后來引申指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壽考)。②長(讀zhǎng),甲骨文是把“老”字上邊的垂發(fā)改為兩根向右上方彎曲的濃密立發(fā)形象。字面義是發(fā)長(cháng)年長(zhǎng),本義是從“老”中分化出的年齡較高之意,后常指四十歲以上有德望的人(長者)。③耊(從“耂”從“矢”),在甲骨文中是“老”在上“矢”在下箭頭指向老人的形象,讀音從“堞”(城垛,是交戰(zhàn)中著箭最多的位置),字面義是“矢中之堞”,會年老生殘之意,也是從“老”分出的一個義項,后引申指八十歲以上的老人。
需要指出的是,“長”因以“镸”注“老”,除了有“年長”之意外,按類義互相授受的特點還兼有“發(fā)長(cháng)”之意。而“考”則具有雙重轉注分化詞義性質(zhì)。這是因為“丂”和“老”各自都是多義詞。若以“丂”注“老”成“考”,區(qū)分的是“老”字“高壽”的詞義;若以“老”注“丂”成“考”,區(qū)分的是“丂”字“壽杖,俗稱拐棍”的詞義。
《說文》明示為轉注的字極少,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其一,《說文》據(jù)形系聯(lián)的體例和資料不足所致。許慎沒有見過甲骨文,據(jù)形系聯(lián)的依據(jù)主要是小篆,小篆之于甲骨文形體變異很大,因此,雖然“長”與“老”實為同部首字卻被分排在“長”、“老”兩部。轉注須涉及兩個字的關聯(lián)關系,而據(jù)形系聯(lián)往往會把同源字分開歸部,所以很難發(fā)現(xiàn)它們的轉注關系。
其二,許慎重形聲輕其它的主觀傾向所致。他把“考”、“耊”和“老”字排在一部,在已經(jīng)指明“考”與“老”轉注關聯(lián)的情況下,卻未指明“耊”也是老的轉注字。再如“句部”,是《說文》中唯一依聲系聯(lián)的一部,下收拘(曲手取物)、笱(捕魚竹具)、鉤(鉤子)三個會意形聲字,其中“拘”和“鉤”都應該是“句”的轉注字,許慎并未指明,而且把“鉤”簡單說成是“從金,句聲”的形聲字。
總之,關于轉注,許慎給后世留下了很多疑惑和爭議。爭議之一是關于轉注產(chǎn)生的原因,后世有諸多見解,在此不宜多述。本文認為,轉注能列入“六書”,必定在漢字演進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诖?,擬從轉注能夠解決的問題入手分析其成為六書之一的成因。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無論是形意文字還是音意文字都只是符號載體,其本質(zhì)功能都是為了記言達意。一般而言,漢字在產(chǎn)生后的一段時期內(nèi),采用象形、指事、會意的方法獲得了一定發(fā)展,但隨著社會生活和語言的發(fā)展,其滿足需要的功能愈顯不足,反映在語言實際中的標志性現(xiàn)象就是大量的假借字、形近字及引申字義的使用。當然,這都是在字少的情況下為細化表達語言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可這卻給理解語義造成了困難,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辦法有兩個。
其一,繼續(xù)加造新字,但急不當用,何況假借字本身就是因為不好造字才采用的,而引申義也都是細虛化動態(tài)性的詞義,都很難用具形征義手段解決。
其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給容易造成歧義的字加注解釋性符號,以達到明確詞義、細化表述的目的。但隨便在一個文句中加注一個與文意不相干的文字符號也容易造成混亂,于是就采取把加注的符號字與被加注字按一個字的構造綴合為一的形式。這樣也就等于通過加注綴合的辦法,轉化制造出了一個由被注字表示類義、加注字表音或參與化義的組合性新字。因此可以認為,轉注的形成主要是由假借字、形近字及引申義在實際使用中所造成的語義問題促成的。
顯然,轉注辦法能有效解決字詞轉性轉義、精細分化、抽象虛化等一系列語義表達難題,同時也直接促成了形聲字的大量出現(xiàn)。其實,用加注轉義法創(chuàng)造新的字詞是世界上各種成熟文字發(fā)展過程中的普遍現(xiàn)象。比如拼音文字中的各種詞綴,其功能都是轉注性質(zhì),只不過由于漢字的轉注是把注解符號與被注解字固化成了一個整體,所以不再明顯罷了。轉注的造意模式處于上升轉折過渡階段,具有突破性質(zhì),屬于由復雜意象圖式向復合意象圖式轉換的過渡形式。
根據(jù)上述分析和認識,試從造意動機角度將轉注具體分為三類進行探討,即:分義性轉注、補位性轉注和分形性轉注。
?。ㄒ唬┓至x性轉注:是通過為類首字加注偏旁、符號的辦法分化聚義字的轉注。
1.禽:常用義項①逮?。虎谇莴F,后專指飛禽。為分化明確兩個詞義,留原字表禽獸,
在原字上加綴義符“扌”轉化出“擒”,表逮住。類似字還有受——授,垂——陲,穵——挖,丂——巧。
2.鬲:義項①空足煮鍋(li);②分隔(ge)。把義符“阝”、加注給“鬲”轉化出“隔”
?。╣e),分擔表示“隔離“,義項①留給原字。有的分義轉注字加注義符后,同時分音變讀。類似字還有罙——①深;②探。襄——①攘;②鑲。雚——觀。氐——①低;②底。塞——①賽;②寨。
?。ǘ┭a位性轉注:這種轉注主要針對假借和被借偏旁原字的補缺替換而成。
1.婁:原字被假借字和偏旁借用,遂另加注義符成“蔞”,以補本字缺位。
2.予:原字被借用為“給予”的“予”,于是又在原字基礎上加注而成“杼”。
類似字還有要——腰;其——箕;求——裘;包——胞;句——勾。
?。ㄈ┓中涡赞D注:這類字本意是加注符號,以補明區(qū)別易混字,但客觀上形成了給象形字、會意字加標義符或聲符,變成了形聲字。這類字曾讓文字學界深感困惑,分形性轉注現(xiàn)象最能證明轉注的作用。
1.玉:原字無“丶”,使用中與“王”分不清,于是加注“丶”相區(qū)別。
2.沒:原字無“氵”,實用中與“殳”形近,遂加注“氵”以區(qū)別。
3.齒:原字上邊無“止”,實用中分不清與“牙”的意義區(qū)別,加注“止(行止)”,表
示是吃飯起止之齒以區(qū)別。
類似字還有茍——敬;萑——雚;冊——笧。
至此,也許有人會提出如何從眾多的形聲、會意甚至指事、象形字中分辨出轉注字的問題。這里先要明確一點,轉注字不是孤立而言,而是相對于與被轉注字(原字)的關聯(lián)而言,因此必須在與原字的比較中甄別,具體來說有三個特征性標準。
其一,詞義的轉聯(lián)性。轉注字的本義,必須與被注原字本義或其下的某個主要義項有直接對應替代的轉聯(lián)關系,而不能僅是與原字的再引申義或義素義有關聯(lián)關系。換言之,轉注字對于原字不能是類義(原字本義)的重復關聯(lián)而是類義分化、替換或補明性關聯(lián)。一般分義性、補位性轉注字的本義外延要小于原字的本義外延,否則就不是轉注關系。
其二,形體的包含性。轉注字與原字在形體上必須直接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聯(lián)關系,其中包括被轉注字的省形和變形體(譬如“長”)。換言之,轉注字的形體范疇必須大于原字的形體范疇,若無關聯(lián)或相等、相反則不是轉注關系。
其三、結構的會意性。轉注字除了個別改筆字(譬如“玉”)之外幾乎又都有明顯的會意性。換言之,沒有會意性的形聲字不會是轉注字。
總之,一個字必須同時符合這些特征才屬于轉注字。下面舉例說明如何辨析轉注字與形聲或會意字的區(qū)別:
?。ㄒ唬?ldquo;頂”和“顛”。《說文》:“頂,顛也,從頁丁聲”;“顛,頂也,從頁真聲”。有人依據(jù)這種與“老”、“考”相同的互訓關系認為二字也是轉注關系。其實這里許慎對“顛”的析形解釋有誤。“頂”是形聲兼會意字,從頁丁聲,丁亦表義,本義為“頭頂”;“顛”是會意形聲字,從“頃,從縣(懸),縣亦聲,字形義是頭歪發(fā)倒,會意義是人走動頭發(fā)上下簸倒(古人束高發(fā)),本義是傾倒、簸動,引申義有頭發(fā)、頭頂。由此可知,顛與頂雖有詞義相同點,但屬引申義與本義的交叉關聯(lián),“頭頂”只是“顛”的引申義,“顛”的本義并非“頂”的義項,此其一;從字形上看,“顛”在形體上并不包含“頂”的形體,也不存在省形因素,此其二。所以說“顛”不是“頂”的轉注字。二者只是類義相通的互訓字。一般而言,原字就是轉注字的構件,若無省形,容易分辨。
?。ǘ?ldquo;婁”和“樓”。“樓”雖然在形體上包含了“婁”的形體,二者也都有會意性,但在詞義關聯(lián)上卻不符合轉注字特征。“婁”字有“高疊”義項,但“樓”字的本義是“疊層房子”,“高疊”這個“婁”字的義項只是“樓”字的義素而不是其本義,因此“樓”不是“婁”的轉注字,而是會意形聲字。
?。ㄈ?ldquo;孝”和“效”。“孝”在實際使用中有“模仿”的義項,而“效”的本義正是模仿,二字在詞義關聯(lián)上符合轉注關系,也都有會意性。但在字形上,“效”的形體并不包含“孝”的形體,也不存在變體問題,因此“效”不是“孝”的轉注字。
綜上可知,轉注形成的字雖然也有類似象形、指事、或改筆的字,比如“長”、“玉”、“勾”,但為數(shù)不多。從總體情況直觀來看轉注字大多表現(xiàn)為形聲字,因此,可以認為形聲字是由轉注字泛化、誘導促成的。
六、形聲
《說文》的解釋為:“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說,形聲是指用兩個字作偏旁組成一個新字,其中一個偏旁標明字義范圍,另一個偏旁標明字的讀音,譬如江、河。
許慎對形聲特征的表述是從一般構成上說的。如果從造意角度分析,形聲字可以細分為三類,即:會意型形聲字、轉注型形聲字和一般型形聲字。
前兩型形聲字,雖然構形上給人以形聲字的印象,但其造意模式卻不是形符和聲符組合的思路,而且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其聲符部分具有參與會意的形素性質(zhì),這在前面已有論述,不再補贅。這里簡單說說一般形聲字。一般形聲字也可以再細分為兩種:一種是純粹形聲字,就是在構字造意時不考慮字的會意性,完全從形符和聲符組合的角度具形造意,最典型的就是化學元素名稱,如:氫、氧、氮、鈉、鉀等;另一種是形聲會意字。這種形聲字,可能出于造意設計,也可能是巧合,總之,由于其客觀構形激活了人們經(jīng)驗意象圖式中的關聯(lián)反應,所以在顯示形聲構造的同時也產(chǎn)生了明顯的會意性。這種形聲字被文字學界稱為“形聲會意字”。比如“摟”字,見到“手”和“婁”的組合圖形,就容易調(diào)動出人們經(jīng)驗意象圖式中手抱蔞的意象,產(chǎn)生會意的效果。形聲的造意模式屬于復合意象圖式,也就是由兩套具形媒介形式共同疊加構成的意象圖式。
綜上所述,本文把漢字發(fā)展演進過程分為三個主體造意模式階段,即象形起步階段、會意突破階段、形聲成熟階段。把其間交叉的指事、假借和轉注歸為三個過渡造意模式,具體對應“六書”的排序為: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所以這樣排列是因為:
首先,會意和形聲的造意思路是兩個不同的思維模式,中間應該有假借和轉注作為過渡環(huán)節(jié)才能實現(xiàn)不同思維模式的轉化,就像指事是象形與會意的過渡環(huán)節(jié)一樣。會意即使在客觀上也造出了一些會意形聲字,但那不是自覺的造意所為,而是漢語同音概率高造成的巧合。
其次,如果會意直接連著形聲,憑藉形聲的強大造字能力,就不會再有假借和轉注的名目多余地排列于“六書”之列。
再次,形聲的方法也產(chǎn)生了不少帶有會意性的形聲字,這說明漢字作為表意的文字體系具有很大范式性的表意歸化效應。
從漢字造意思維模式由簡單意象圖式(象形),到復雜意象圖式(會意),進而演變到復合意象圖式(形聲)的過程看,形聲應該是漢字造字法發(fā)展的最后方法,它造出的字最多,是健全漢字體系最強大最簡練的構造模式,也是造字法發(fā)展到完全成熟階段的標志。因此,形聲作為具有表音表義雙重具形性質(zhì)的造字法,能在漢字依形表意的演化進程中最終形成,不會是突現(xiàn)的,它應該有一個積累漸變、過渡轉化的曲折過程。
(本文作者:李強轉自貴州語言文字網(wǎng))


